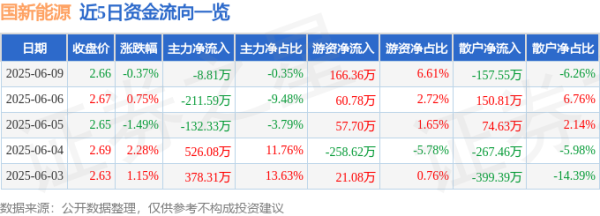我上一辈无锡人吃虾,颇求风雅,觉得虾大了肉多兴启网,但没味,恨不得虾越小越好。
最好的虾,须当长不盈寸,鲜活出水,加姜与葱,水煮到红又透明,剥壳来吃,有鲜甜味。
吃不到鲜虾的,也愿意迁就炒虾仁。乡下吃露天宴席,若没一盘好虾仁,会被人抱怨不上路:鱼太清淡,肉太俗腻;炒虾仁方是有味有格,能登大雅之堂。一大盘虾仁上来,汁滑肉厚,不等动筷,大家先要道声好。
然而好虾仁啊,是不该这么炒的。好虾仁,应该一次炒四五个,一晃一铲,三铲起锅,晶莹剔透,才是好虾仁啊!——跟我说这些的,是我们乡下的一个晁师傅。
无锡话里,晁发音类似于潮,大家嘴顺,都叫他炒师傅了。
炒师傅是个流动厨子。倒不是他无业,是没哪家雇得下他。
我们那里乡下人,惯吃宴席,需要大师傅掌勺;在乡下,三样东西是看声誉、一个地方人共用的:军乐队、修棕棚的、宴席厨子。
各家办红白事,屋里到院中,能摆几桌摆几桌,偶尔还搭凉棚;几桌到十几桌的菜,炒师傅能一手包办:他与徒弟开着卡车,带着煤气罐、锅铲、炉灶、食材们到来,他就地指挥徒弟们,分门别类,摆开家伙,做菜,自己拳不离手曲不离口,下场颠勺。
炒师傅有一道炒虾仁,名闻乡里;一锅能炒出十盘子分量的虾仁,薄油薄芡,不糊不生。虾仁上桌,炒师傅就会去跟诸位敬杯黄酒,乡下大家也跟他举杯,轰然问好。
但就是这么个炒师傅兴启网,跟我说:虾仁,要炒小盘的才对呵。
当然不是单独跟我说的。那时我一个远房堂哥的孩子满月酒,堂哥是炒师傅的寄名干儿子,还受炒师傅帮忙,在高速公路旁开饭馆,算是自己人。

那天炒师傅等大家散了,剩下的亲戚在席后打麻将吃瓜子的时候,似乎高了兴,多喝了几杯,听人夸他虾仁炒得好,才说了这几句。当然与一般世外高人不同,炒师傅是边炒边说的——光说不练假把式,他老人家现场炒了一盘虾仁,让我们看看。
他的某些故事,也是那天听来的。
炒师傅少年时,去无锡某已经被合并的老馆子学艺。他的师父们那时跟他念叨“炒虾仁要小盘小碟地炒,一次炒四五个,才能火候均,又不老”,师父的话,他听着,但没啥实践机会。
师父们以前,据说是给面粉厂里有钱人炒虾仁的;炒师傅自己学艺出师时,许多店都国营了,来饭店里吃炒虾仁的不喜欢小盘虾仁,喜欢大盘子大碗。老师父们有些脑子转不过筋来,私下里感叹手艺没处用,“个么哪亨呢,唔不规矩了!”
炒师傅这时得志了:他年轻,体力好,眼睛也还好——那会儿的厨房里很靠眼睛——大锅炒虾仁,就都归他来了:炒大锅是需要点体力的,师父们也乐得让他使。
当然,炒师傅并不全然听师父们的。年轻嘛,爱吃肉嘛,老陆稿荐的酱方、三凤桥的排骨,年轻人爱吃这个;鱼啊虾啊,味道淡。炒师傅年轻时,大锅炒虾仁,也没觉得不好;小锅炒虾仁,也没觉得多好。哎,不管了。炒就炒啦。
机关食堂需要人才,他被征召去了。大锅炒虾仁,又快又好,搞得邻近单位人尽皆知,都来他们食堂吃,大家都说:年轻人脑筋活,很好,不像他的师傅们,那些老头子,炒虾仁一小盘一小盘……
后来设一个疗养院,需要在机关食堂师傅里,给老干部们配一个厨师。据说有个老干部要求特别刁:要会做白灼狮子头——嫌红烧的有酱油酸气;要会小盘清炒虾仁——不要大锅炒的,腻,“黏滋黏啦”!机关食堂一问,只有炒师傅会小锅炒虾仁。
炒师傅觉得自己走了好运:因为会大锅炒虾仁,进了机关食堂;因为会小盘炒虾仁,他跟了领导。好。
跟了老干部后,炒师傅的条件大为改善:不说锦衣玉食,至少离温饱近,离烟火远。红烧肉和肉酿面筋吃多了,终于到了不怎么爱吃肉的年岁。也开始懂得喝口清茶、吃口鲜鱼的美妙——以前是听师父说好,跟着附和“味道鲜!”到有年纪后,真懂得咂摸滋味了。
也终于晓得了:小锅炒虾仁,确实比大锅炒虾仁要好吃。
他怎么到乡下来的呢?
他侍奉的那位老干部,后来出了点事,要“交代问题”。交代问题时,炒师傅作为厨师,当然要报一遍老干部的饮食,他说了,人家就总结,“某某每顿饭都要吃鲜鱼鲜虾,还是吃小灶,作风不好”,这句话听得炒师傅背上生凉。
好在老干部出事,他没遭连累;作为小灶厨子,还是被分配去了其他单位,但大家说起来,总是侧目:“就是伊个宁,开小灶格,听说伊炒虾仁,拿个领导都炒了”……其他单位的领导,也许是迷信吧,就不让他炒虾仁了。
所以他没到退休年纪,就自动请调到了乡下的机床厂,远离了机关,没几年又干上了私厨子。乡下天高皇帝远,也没人管,得了。他说这样好,自在。
这些故事,有些是炒师傅当天说的,有些是我堂哥后来补齐的。至少当天我还没完全明白这些,只记得那盘小锅炒的虾仁,确实是我吃过,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盘好虾仁。
翼牛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